央视《面对面》:专访浙江省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

中国园林网6月11日消息:CCTV.com消息(面对面):
人物介绍:傅企平,1948年出生,浙江奉化人,滕头村党委书记,曾担任滕头村党委副书记十七年,个人主张建设立体、生态农业,并致力与保护滕头村的生态环境,带领村民走上生态致富之路而受到外界关注。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地区的奉化市萧王庙街道的滕头村。全村人口不足800人,2005年的社会总产值却达到18.2亿元人民币,人均纯收入15600元。虽然村子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却拥有全球生态500佳的称号。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村子,因为什么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里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这里的村民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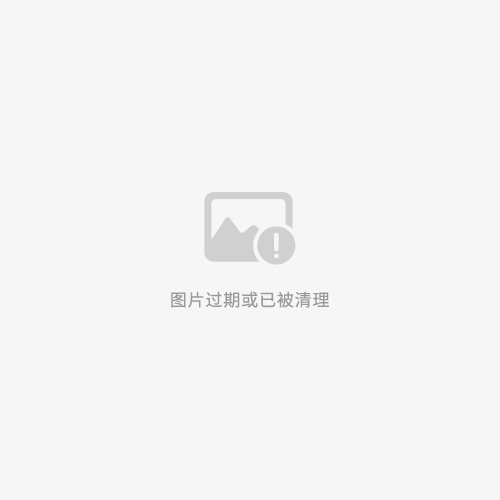
记者:那村民现在都干什么呢?
傅企平:村民现在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干部,有的搞工业,有的搞农业,搞第三产业也有。
记者:那作为滕头村民来说,他到底有哪些待遇啊?
傅企平:滕头村的村民,年纪大的有退休金,一般现在最低的是一个人6000块一年。
记者:六千块。
傅企平:哎,一年,高的一万多,因为贡献有大小的。还有很多保险,有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很多的保险,还有大病的保险,还有读书我们都是免费的,还有一些生病的,大病的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村里都有补助,所以我们这里现在讲,没有暴发户 也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小康户。
家家都是小康户,这句话并不能完全体现滕头村村民生活的改变。这是一部以滕头村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了不起的村庄》,影片中80%以上的场景都是滕头的实景,美丽的乡村风光让看过影片的观众印象深刻。 目前滕头村村民不足800人,村民中有将近500人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都在村里的工厂工作,每个月像大多数城里人那样用银行卡领工资。


记者:你们现在跟城市一般的城市有什么区别?
傅企平:现在很多地方和提出要城乡一体化,当然有的地方要城市跟农村一样。但是我们很多的地方,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城市了。像我们的奉化、宁波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们认为还不如我们。
记者:比方说?
傅企平:比如说我们的水很清,我们的空气很清新的,我们的老百姓人情味很弄。城市里面隔壁,楼上楼下都不说话的。我们平时都是很和谐的。
与其他村不同的是,进滕头村参观,需要购买一张门票,这在中国的农村中也算是第一家。
记者:门票是多少钱一张啊?
傅企平:原来我们在1999年五块,十块,二十块,三十块,四十块,现在是五十块,越高来的人越多。(去年我们观光农业的门票就有610万,旅游的总额的收入有2800万,今年我们的门票能超过800万,总额的收入肯定会超过3500万。
记者:那参观参观,你还要人家花钱来买门票,当时就没有顾虑吗?
傅企平:当时有顾虑啊,一开始搞的时候一部分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年纪大的他们想不通,你农村里面那些花花草草,你卖门票?谁能来啊?你不可能的,异想天开的。
记者:看什么呢?有什么值得看的,五十块钱?

傅企平:50块钱,你可以玩一天。你看看鸽子、鸭子、笨猪赛跑,还有老虎、狮子还有一些杂技,还有一些婚庆,还有很多参与的东西,你采草莓啊,采小黄瓜啊,还有牛耕地。
记者:那你跟游乐园有什么不一样?
傅企平:我们这里主要是具有三农的特色,我们有农村建筑,我们有一些农业的东西,现在很多城市里面,不要讲小朋友,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马啊,什么是牛啊,什么是小麦,什么是韭菜,他们也分不清的,他们到滕头村来看了以后,哦,这个就是这样的,他们很高兴。[分页]
这是村里的一项传统表演项目——笨猪赛跑,农村里常见的家畜、家禽在滕头村却成了一个个表演项目。每隔一段时间,村里还举办一场被村民们称为“乡村嘉年华”的活动,在这里除了能够体会乡村生活之外,还可以在滕头村感受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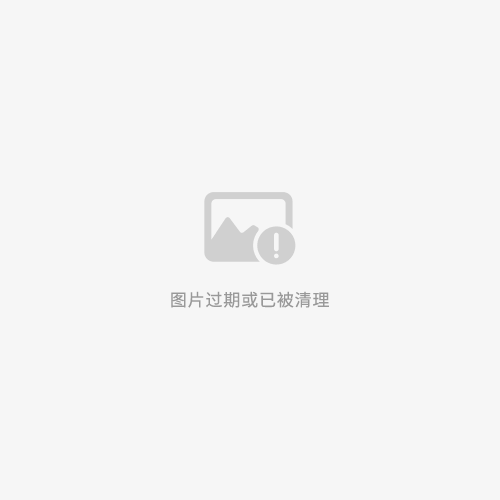
傅企平:这里是婚庆园。
记者:字写在瓜上?
傅企平:对自己写上去。
记者:南瓜长大以后 他就可以摘走。
傅企平:对 摘走,你看 这个就写着,是什么时候写的 都有时间,这个里面可以拜堂。
记者:干什么?
傅企平:结婚,拜堂的。
如今到滕头村举办一场生态民俗婚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来自周边城市里的年轻人的选择,在网络上搜索这个普通的小乡村,有近10万条的相关信息。其中有近万条是关于滕头村的游记,很多来过滕头村的游客把它称为“世外桃源”。那么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以前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老书记:老婆娶不进来。都是泥草屋。
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却成为一个尴尬的先进村。
傅企平:外面是很火红的,里面是穷的。
今年82岁的傅嘉良在滕头村当了三十年的村支书,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滕头村的建设,对于40年前的滕头村傅嘉良记忆犹新。
记者:当时村里是什么情况?
老书记:村里很穷很穷。
记者:怎么个穷法?
老书记:老婆娶不进来,都是泥草屋,老百姓住的是泥屋、草屋、小屋。我们这个地方地势很低,十田九荒。一场大雨下了就淹了,旱的时候被晒死,雨的时候被淹死。
傅企平:我们过去也有些民谣的。
记者:什么民谣?
傅企平:叫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
记者:当时的人均收入有多少?
傅企平:一年做到头,没有几十块钱,就是靠几亩土地。大水一发,一涝以后,粮食被水淹了以后,就基本上没什么收入了。
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滕头村开始改土造田,很快滕头村成为了省里甚至全国的“学大寨”先进村。这种先进也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周边村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滕头村村民渴望致富的愿望也越发强烈。但是“学大寨”的先进荣誉并没有给村民带来更加富裕的生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却成了村民致富的包袱。
傅企平:后来农业稳定了,但是工业没上去,那个时候咱们是农业大寨的先进单位,不能搞资本主义,养一只鸡是社会主义,你养三只就是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你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了,所以那个时候滕头村也是先进单位。外面是很红的,里面是很空的。
记者:怎么讲?
傅企平:外面是看上很火红的,里面实际上很穷的。
当时土地已经分产到户,种什么,怎么种由村民决定。很多地方村民觉得种地不划算,有的干脆种一季荒一季,或者直接就把土地荒着。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让土地闲置、荒掉实在是件说不过去的事情,但是如何解决这些土地和因土地赋闲的村民,老书记傅嘉良考虑把分到户的土地再集中起来,这在当时无疑是个风险之举。
傅企平:搞农业、搞粮食,没有钱可赚的,大家都土地都荒掉了,那不行,我们看着土地心疼的。那么就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开始三户,我也搞了一户,老书记当时就说企平呀你也去搞一户。这个土地荒掉不行了。当时粮食价格很低。
记者:那挣不到钱还合起来种地,种那么多粮食怎么考虑呢?
傅企平:当时村里头有补贴的,村里补一点。
记者:村里为什么要补呢?什么考虑呢为什么要给补贴?
傅企平:因为粮食国家很重视,你不能荒地。
记者:那与滕头村有什么关系?
傅企平:滕头村是农业学大战的先进单位啊,土地荒了以后,上级领导要抓你的。
记者:村民的思想通吗?这个地又和起来。
傅企平:土地没有人种啊?
记者:但是使用权是我的。你收回去了。
傅企平:我们收回去还给他钱了。
记者:怎么运作呢?
傅企平:一亩土地给他现在是550块,运作呢,我们把土地集中以后,成立一个农业公司。[分页]
1986年,村里成立了农业公司,这是滕头村农业产业化的开始。然而农业公司怎么运作,怎样才能让闲置荒芜的土地里长出黄金来呢?
记者:谁来做这个决策,我们种什么,不种什么?
傅企平:那么就是农业公司,根据市场的调查以后种什么好。还有一个根据我们滕头村的土地,土壤的结构,这里适合种什么东西,有些东西我们这里不能种。农业公司就可以一块一块的分开,承包。我们也种粮食的,集中种粮食,因为粮食附加值太低,不划算,那么就是慢慢的就搞多种经济了。
在集体的土地种什么一直是傅企平和农业公司苦心钻研的问题,他们





 浙公网安备 33010402003154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402003154号